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大雅稅務爭議解決及訴訟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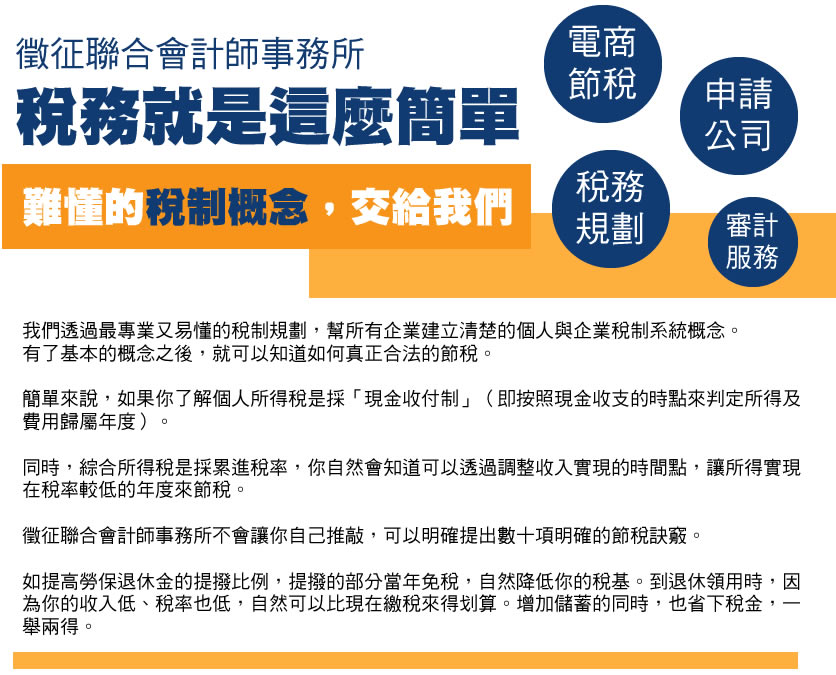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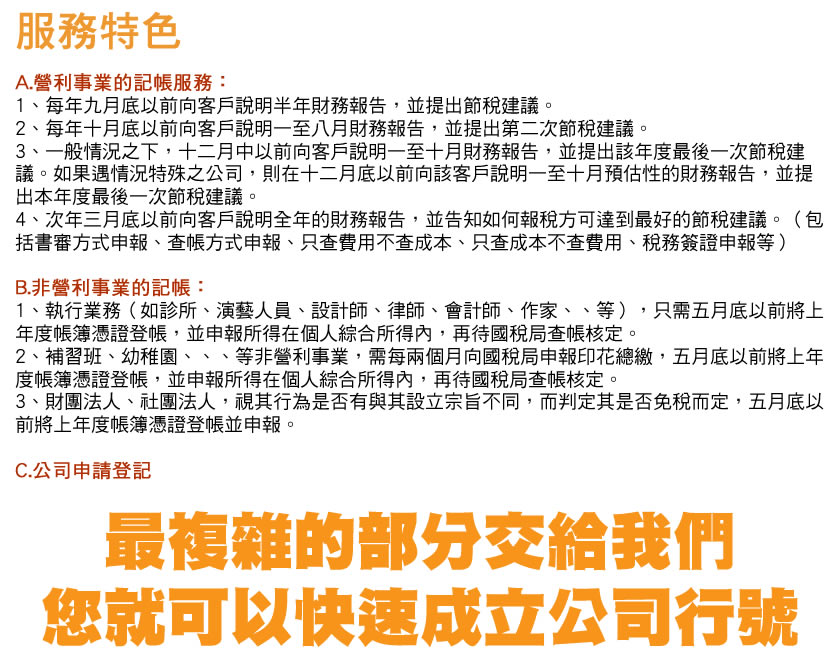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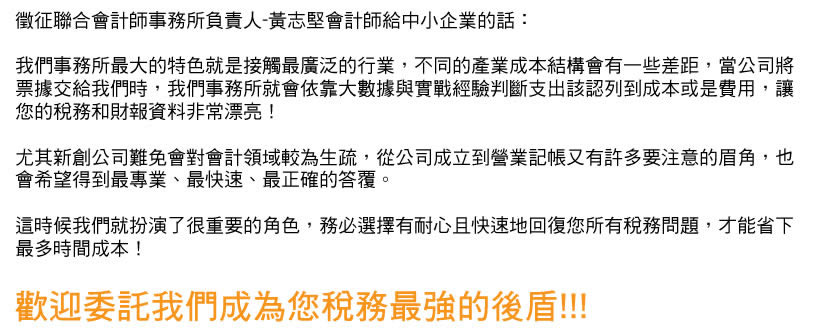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北區稅務及電子商務規劃, 台中南屯鄭裕民會計師, 台中中區企業重組會計服務推薦
史鐵生:我的幼兒園 五歲,或者六歲,我上了幼兒園。有一天母親跟奶奶說:“這孩子還是得上幼兒園,要不將來上小學會不適應。”說罷她就跑出去打聽,看看哪個幼兒園還招生。用奶奶的話說,她從來就這樣,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親就打聽到了一所幼兒園,剛開辦不久,離家也近。母親跟奶奶說時,有句話讓我納悶兒:那是兩個老姑娘辦的。 母親帶我去報名時天色已晚,幼兒園的大門已閉。母親敲門時,我從門縫朝里望:一個安靜的院子,某一處屋檐下放著兩只嶄新的木馬。兩只木馬令我心花怒放。母親問我:“想不想來?”我堅定地點頭。開門的是個老太太,她把我們引進一間小屋,小屋里還有一個老太太正在做晚飯。小屋里除兩張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張桌子和一個火爐。母親讓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鏡的那個叫孫老師,管另一個瘦些的叫蘇老師。 我很久都弄不懂,為什么單要把這兩個老太太叫老姑娘?我問母親:“奶奶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親說:“沒結過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結過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這樣的解釋。結婚嘛,不過發幾塊糖給眾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別的作用嗎?在我想來,女人年輕時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會有“老姑娘”這不倫不類的稱呼?我又問母親:“你給大伙買過糖了嗎?”母親說:“為什么?我為什么要給大伙買糖?”“那你結過婚嗎?”母親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沒結過婚就敢有你了嗎?”我越發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這幼兒園遠不如我的期待。四間北屋甚至還住著一戶人家,是房東。南屋空著。只東、西兩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塊黑板連桌椅也沒有,孩子們每天來時都要自帶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幾個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歲,小的三歲。上課時大的喊小的哭,老師喝斥了這個哄那個,基本亂套。上課則永遠是講故事。“上回講到哪兒啦?”孩子們齊聲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舉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實已經尿完。一個故事斷斷續續要講上好幾天。“上回講到哪兒啦?”“不-聽-話-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課一窩蜂都去搶那兩只木馬,你推我搡,沒有誰能真正騎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發明出另一種游戲,“騎馬打仗”:一個背上一個,沖呀殺呀喊聲震天,人仰馬翻者為敗。兩個老太太--還是按我的理解叫她們吧--心驚膽戰滿院子里追著喊:“不興這樣,可不興這樣啊,看摔壞了!看把劉奶奶的花踩了!”劉奶奶,即房東,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辦幼兒園。但“騎馬打仗”正是熱火朝天,這邊戰火方歇,那邊烽煙又起。這本來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來,又有了懲罰戰俘的規則。落馬者僅被視為敗軍之將豈不太便宜了?所以還要被敲腦蹦兒,或者連人帶馬歸順敵方。這樣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對叛徒的更為嚴厲的懲罰。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兩個人壓著,倒背雙手“游街示眾”,一路被人揪頭發、擰耳朵。天知道為什么這懲罰竟至比騎馬打仗本身更具誘惑了,到后來,無需騎馬打仗,直接就玩起這懲罰的游戲。可誰是被懲罰者呢?便涌現出一兩個頭領,由他們說了算,他們說誰是叛徒誰就是叛徒,誰是叛徒誰當然就要受到懲罰。于是,人性,在那時就已暴露:為了免遭懲罰,大家紛紛去效忠那一兩個頭領,阿諛,諂媚,惟比成年人來得直率。可是!可是這游戲要玩下去總是得有被懲罰者呀。可怕的日子終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長著的年齡一樣,必然來臨。 做叛徒要比做俘虜可怕多了。俘虜尚可表現忠勇,希望未來,叛徒則是徹底無望,忽然間大家都把你拋棄了。五歲或者六歲,我已經見到了人間這一種最無助的處境。這時你唯一的祈禱就是那兩個老太太快來吧,快來結束這荒唐的游戲吧。但你終會發現,這懲罰并不隨著她們的制止而結束,這懲罰擴散進所有的時間,擴散到所有孩子的臉上和心里。輕輕的然而是嚴酷的拒斥,像一種季風,細密無聲從白晝吹入夜夢,無從逃脫,無處訴告,且不知其由來,直到它忽然轉向,如同莫測的天氣,莫測的命運,忽然放開你,調頭去捉弄另一個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兒園。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開始裝病,開始想盡辦法留在家里跟著奶奶,想出種種理由不去幼兒園。直到現在,我一看見那些哭喊著不要去幼兒園的孩子,心里就發抖,設想他們的幼兒園里也有那樣可怕的游戲,響晴白日也覺有鬼魅徘徊。 幼兒園實在沒給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倒是那兩個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記憶里,一個胖些,一個瘦些,都那么慈祥,都那么忙碌,慌張。她們怕哪個孩子摔了碰了,怕弄壞了房東劉奶奶的花,總是吊著一顆心。但除了這樣的怕,我總覺得,在她們心底,在不易覺察的慌張后面,還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么呢?說不清,但一定更沉重。 長大以后我有時猜想她們的身世。她們可能是表姐妹,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們一定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們都彈得一手好風琴,似可證明。我剛到那幼兒園的時候,就總聽她們向孩子們許愿:“咱們就要買一架風琴了,幼兒園很快就會有一架風琴了,慢慢兒地幼兒園還會添置很多玩具呢,小朋友們高不高興呀?”“高——興!”就在我離開那兒之前不久,風琴果然買回來了。兩個老太太視之如珍寶,把它輕輕抬進院門,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锃亮,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孩子們圍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后蘇老師和孫老師互相推讓,然后孩子們等不及了開始嘁嘁嚓嚓地亂說,然后孫老師在風琴前莊重地坐下,孩子們的包圍圈越收越緊,然后琴聲響了孩子們歡呼起來,蘇老師微笑著舉起一個手指:“噓——噓——”滿屋子里就又都靜下來,孩子們忍住驚嘆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動……那天不再講故事,光是聽蘇老師和孫老師輪流著彈琴,唱歌。那時我才發覺她們與一般的老太太確有不同,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里都涌現著天真。那琴聲我現在還能聽見。現在,每遇天真純潔的事物,那琴聲便似一縷縷飄來,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幻現出一片陽光,像那琴鍵一樣地跳動。 我想她們必是生長在一個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們的父母一定溫文爾雅善解人意。她們就在那樣的琴聲中長大,雖偶有輕風細雨,但總歸晴天朗照。這樣的女人,年輕時不可能不對愛情抱著神圣的期待,甚至難免極端,不入時俗。她們竊竊描畫未來,相互說些臉紅心跳的話。所謂未來,主要是一個即將不知從哪兒向她們走來的男人。這個人已在書中顯露端倪,在裝禎精良的文學名著里面若隱若現。不會是言情小說中的公子哥。可能會是,比如說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但絕不是渥倫斯奇或卡列寧一類。然而,對未來的描畫總不能清晰,不斷的描畫年復一年耗損著她們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話說:她們真正是“小布爾喬亞”之極,在那風起云涌的年代里做著與世隔絕的小資產階級溫情夢。大概會是這樣。也許就是這樣。 假定是這樣吧,但是忽然!忽然間社會天翻地覆地變化了。那變化具體是怎樣侵擾到她們的生活的,很難想象,但估計也不會有什么過于特別的地方,像所有衰敗的中產階級家庭一樣,小姐們惟驚恐萬狀、睜大了眼睛發現必須要過另一種日子了。顛沛流離,投親靠友,節衣縮食,隨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體會著沉浮與炎涼……然后,有一天時局似乎穩定了,不過未來明顯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樣任性地描畫。以往的描畫如同一疊精心保存的舊鈔,雖已無用,但一時還舍不得扔掉,獨身主義大約就是在那時從無奈走向了堅定。 她們都還收藏著一點兒值錢的東西,但全部集中起來也并不很多,算來算去也算不出什么萬全之策,惟知未來的生活全系于此。就這樣,現實的嚴峻聯合起往日的浪漫,終于靈機一動:辦一所幼兒園吧。天真爛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歡樂。幼兒園嗎?對,幼兒園!與世無爭,安貧樂命,傾余生之全力澆灌并不屬于我們的未來,是嗎?兩個老姑娘仿佛終于找回了家園,云遮霧障半個多世紀,她們終于聽見了命運慷慨的應許。然后她們租了一處房子,簡單粉刷一下,買了兩塊黑板和一對木馬,其余的東西都等以后再說吧,當然是錢的問題……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回那幼兒園去看過一回。果然,轉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里桌椅齊備,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幾倍。房東劉奶奶家已經遷走。一個年輕女老師在北屋的廊下彈著風琴,孩子們在院子里隨著琴聲排練節目。一間南屋改作廚房,孩子們可以在幼兒園用餐了。那個年輕女老師問我:“你找誰?”我說:“蘇老師和孫老師呢?”“她們呀?已經退休了。”我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說哪是什么退休呀,是她們的出身和階級成分不適合教育工作。后來“文革”開始了,又聽說她們都被遣送回原籍。 “文革”進行到無可奈何之時,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見孫老師。她的頭發有些亂,直著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張。我叫了她一聲,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說出我的名字,“您不記得我了?”她臉上死了一樣,好半天,忽然活過來:“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給冤枉了呀。”我故作驚訝狀:“冤枉了?我?”其實我已經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來了。蘇老師跟我說,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傷重了吧?” 那是我臨上小學前不久的事。在東屋教室門前,一群孩子往里沖,另一群孩子頂住門不讓進,并不為什么,只是一種游戲。我在要沖進來的一群中,使勁推門,忽然門縫把我的手指壓住了,疼極之下我用力一腳把門踹開,不料把一個女孩兒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兒鼻子流血,頭上起了個包,不停(www.lz13.cn)地哭。蘇老師過來哄她,同時罰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別的孩子們上課,心里委屈,就用蠟筆在糊了白紙的窗欞上亂畫,畫一個老太太,在旁邊注明一個“蘇”字。待蘇老師發現時,雪白有窗欞已布滿一個個老太太和一個個“蘇”。蘇老師顫抖著嘴唇,只說得出一句話:“那可是我和孫老師倆糊了好幾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別了幼兒園,理由是馬上就要上小學了,其實呢,我是不敢再見那窗欞。 孫老師并沒有太大變化,惟頭發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入慌張。我問:“蘇老師呢,她好嗎?”孫老師抬眼看我的頭頂,揣測我的年齡,然后以對一個成年人的語氣輕聲對我說:“我們都結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為以我的年齡不合適再問下去,但從此心里常想,那會是怎樣的男人和怎樣的家呢?譬如說,與她們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與那陽光似的琴聲能否和諧? 史鐵生作品_史鐵生散文集 史鐵生:故鄉的胡同 史鐵生:奶奶的星星分頁:123
杏林子:《生命的極限》 你可能知道你的身高 你的體重 你眉毛的位置 你指節的長短 然而 你卻不知道 你的韌力有多長 你的能力有多大 你的潛力有多深 你的耐力有多久 你能學會多少,用多少 愛多少,付出多少 原諒多少,發揮多少 除非你嘗試 我們的愛心 都是從最不可愛的人身上培養出來的 我們的信心 都是從一次次失敗中學習出來的 我們的忍耐 都是從最不堪的環境里磨練出來的 我們的潛力 都是從最大的壓力下發揮出來的 我們不斷探索 不斷學習 不斷發現 不斷獲得 不斷為克服重重難關而殫精竭慮 不斷為經歷一個新的里程而歡愉 就在這不斷的挑戰中 將我們的生命極限擴至無限 我們的力量和愛 也無限 “上帝什么時候會接我去,我不知道。 對我而言(www.lz13.cn),每一天都是生命的最后一日, 每一天也是生命的第一日。 因為是最后一日,便倍覺珍惜寶貴; 因為是第一日, 便仍有無限的期盼與展望。” ──杏林子 杏林子作品_杏林子散文集 杏林子:恒久的愛 杏林子:家分頁:123
魯迅:堅壁清野主義 新近,我在中國社會上發現了幾樣主義。其一,是堅壁清野主義。 “堅壁清野”②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業,所以這話不是從兵家得來,乃是從別的書上看來,或社會上聽來的。聽說這回的歐洲戰爭時最要緊的是壕塹戰,那么,雖現在也還使用著這戰法——堅壁。至于清野,世界史上就有著有趣的事例:相傳十九世紀初拿破侖進攻俄國,到了墨斯科時,俄人便大發揮其清野手段,同時在這地方縱火,將生活所需的東西燒個干凈,請拿破侖和他的雄兵猛將在空城里吸西北風。吸不到一個月,他們便退走了。 中國雖說是儒教國,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丘未之學也。”③但上上下下卻都使用著這兵法;引導我看出來的是本月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據說,教育當局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生有傷風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學生往游藝場和公園,并通知女主家屬,協同禁止。④自然,我并不深知這事是否確實;更未見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當局之意,是因為娛樂場中的“有傷風化”情事,即從女生發生,所以不許其去,還是只要女生不去,別人也不發生,抑或即使發生,也就管他媽的了。 或者后一種的推測庶幾近之。我們的古哲和今賢,雖然滿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無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結果是:收起來。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專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二,是器宇只有這么大,實在并沒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經濟法,只有將錢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樣。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誨盜,冶容誨淫”⑤,就是說子女玉帛的處理方法,是應該堅壁清野的。 其實這種方法,中國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過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見男人和賣力氣的女人,很少見所謂上流婦女。但我先在此聲明,我之不滿于這種現象者,并非因為預備遍歷中國,去竊窺一切太太小姐們;我并沒有積下一文川資,就是最確的證據。今年是“流言”鼎盛時代,稍一不慎,《現代評論》上就會彎彎曲曲地登出來的,所以特地先行預告。至于一到名儒,則家里的男女也不給容易見面,霍渭崖的《家訓》⑥里,就有那非常麻煩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構造圖。似乎有志于圣賢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應該看作游藝場和公園;現在究竟是二十世紀,而且有“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的教育總長⑦,實在寬大得遠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錮婦女,走在外面,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這和我們的古哲和今賢之意相左,或者這種風氣,倒是滿洲人輸入的罷。滿洲人曾經做過我們的“圣上”,那習俗也應該遵從的。然而我想,現在卻也并非排滿,如民元之剪辮子,乃是老脾氣復發了,只要看舊歷過年的放鞭爆,就日見其多。可惜不再出一個魏忠賢⑧來試驗試驗我們,看可有人去作干兒,并將他配享孔廟。 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為之事,“收起來”卻是管牢監的禁卒哥哥的專門。況且社會上的事不比牢監那樣簡單,修了長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溝高壘,都沒有用處的。未有游藝場和公園以前,閨秀不出門,小家女也逛廟會,看祭賽,誰能說“有傷風化”情事,比高門大族為多呢? 總之,社會不改良,“收起來”便無用,以“收起來”為改良社會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車往奉天。這道理很淺顯:壁雖堅固,也會沖倒的。兵匪的“綁急票”⑨,搶婦女,于風化何如?沒有知道呢,還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頌德的! 其實,“堅壁清野”雖然是兵家的一法,但這究竟是退守,不是進攻。或者就因為這一點,適與一般人的退嬰主義相稱,于是見得志同道合的罷。但在兵事上,是別有所待的,待援軍的到來,或敵軍的引退;倘單是困守孤城,那結果就只有滅亡,教育上的“堅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么呢?照歷來的女教來推測,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還能茍安時候,所謂男子者儼然地教貞順,說幽嫻,“內言不出于闊”,“男女授受不親”⑩。好!都聽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罷。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襲來了,足下將何以見教呢?曰:做烈婦呀! 宋以來,對付婦女的方法,只有這一個,直到現在,還是這一個。 如果這女教當真大行,則我們中國歷來多少內亂,多少外患,兵燹頻仍,婦女不是死盡了么?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際,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于是生育子孫,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斷,但到現在還很有帶著奴氣的人物,大概也就是這個流弊罷。“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傳,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闊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來,因此還只得奉這為至寶。更昏庸的,便以為只要意見和這些歧異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當然的事。但最近,孫美瑤據守抱犢崮,其實倒是“堅壁”,至于“清野”的通品,則我要推舉張獻忠(www.lz13.cn)。 張獻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誰也知道,誰也覺得可駭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殺完百姓之后,便令AB殺C,又令A殺B,又令A自相殺。為什么呢?是李自成⑾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殺完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正如傷風化是要女生的,現在關起一切女生,也就無風化可傷一般。 連土匪也有堅壁清野主義,中國的婦女實在已沒有解放的路;聽說現在的鄉民,于兵匪也已經辨別不清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魯迅作品_魯迅散文集_魯迅名言全集 魯迅:“友邦驚詫”論 魯迅讀書的名人名言分頁:123
ACC711CEV55C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